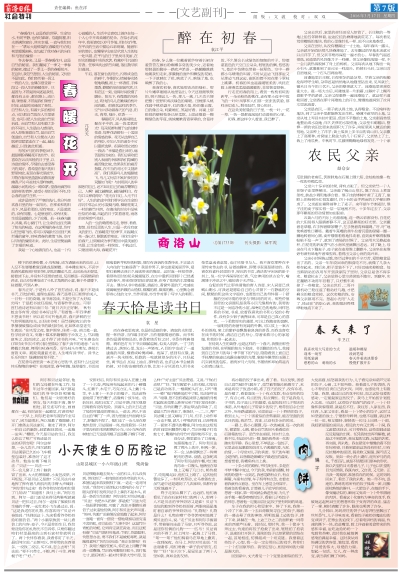农民父亲
文章字数:1299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责任田没人经管了。长庄稼的一等地让给四邻耕种着,边边拉拉的瘠薄地就荒芜了。每次看见荒草糟践的地块,我的心里像针扎一样,说不出来地难受。
父亲在世时,从没有糟蹋过一寸土地。每年春风一露头,父亲就开始收拾那几块瘠薄地了。去年翻过的冬地本来就可以点洋芋了,但父亲非要再深挖一遍才放心。早春的气温还很低,河道里的风仍像刀子一样硬。但父亲像挖战壕一样,不一会儿就热得脱掉了身上的棉袄。父亲每次从地下掏出一块小石头,就像拣到了金元宝一样高兴。扔掉石头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一个石头四两油哩。
河滩地里长庄稼,长得更多的是杂草。尽管父亲的板锄抡得呼呼生响,杂草还是悄悄地从地缝里钻出来,见风就长;锄禾日当午的三伏天,父亲的孽果就大了。河滩地里更喜欢涨大水。涨一场大水后,河滩地里一片狼藉,庄稼叶子上糊弄着脏乎乎的淤泥,父亲又得重修一遍河滩地了。就这样天道轮回着,父亲洒在那片河滩地上的汗水,慢慢地滋润到了汝河水里流淌着。
父亲是农民,一辈子就认得土地,认得粮食。不论啥样的地块,到了父亲手里都能焕发出生机。瘠薄不耐旱的土地,父亲从坡上弄回木拉叶肥田;低洼不平整的土地,父亲削高垫低地整治成水浇地;年久失修的水毁荒地,父亲垒石砌堰后,整修一新的农田比原来的面积大了许多;沟垭里别人嫌远的抛荒地,父亲种上了洋芋;黄土梁顶上多半亩的高山田,父亲撒上了高粱种;对窝崖上脸盆大的几个石窝子,父亲垫上了土,栽上了南瓜秧。中秋时节,瓜藤黑黝黝地绿得发亮,一个个滚瓜肚圆的老南瓜,笑眯眯地在石堰上晒太阳,金灿灿地像一枚一枚的劳模奖章。
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背有点驼了。但父亲依然一个人在堡子洼里修梯田。父亲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在山上煮面条吃,缺盐少调和地凑合着。堡子洼的烤树叶黄了又青了,崖畔上的柿树叶红得发紫时,四个台阶近乎两亩的水平梯田修成了。父亲赶在霜降前种上了麦子。来年端午节割麦时,堡子洼的麦子厚实得一层一层地割不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那年碾场的劳动情景如在眼前。
五黄六月的天际上光溜溜地,连一绺云彩都没有,白花花的太阳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这正是碾场的好光景。父亲戴着老草帽,右手挥着柳条鞭子,左手挽着青麻缰绳,“吁、吁”地使唤着牲口碾场。戴着牛笼嘴的黄牛拉着沉重的碌碡一圈一圈地转着同心圆,麦秆嗤嗤啦啦地抖动着,直到麦秆碾得服服帖帖不发一声了,就到了清场的时候了。父亲用木叉撩起麦秆,白花花的新麦香气在小南风里就飘出老远。到了晚上,母亲在月光下簸麦子,孩子家在麦草堆上翻跟斗,父亲坐在麦堆旁有滋有味地听着秦腔戏,看得出父亲心底的高兴来。
父亲小时候挨过饿,经历过种田的千辛万苦,爱惜粮食是出了名的。父亲一年年收回来的粮食吃不完,就做了几条大柜存起来。到后来,柜子里装不下了,只好忍痛卖掉粮食。每当购销站的农用车开到我家院子里时,父亲总是舍不得多卖。粮食拉走了,父亲觉得心里空荡荡地不踏实。到晚年,实在翻晒不动陈年旧粮了,只好整车卖掉了一些粮食。父亲去世后,二哥开着机动三轮往返了粮站好几趟,才把剩余的粮食卖掉。这次卖粮的钱,安葬父亲都用不完。想起小沈阳“人走了,钱还在”的伤心话,我的眼泪哗哩哗啦地流下来了。
父亲在世时,从没有糟蹋过一寸土地。每年春风一露头,父亲就开始收拾那几块瘠薄地了。去年翻过的冬地本来就可以点洋芋了,但父亲非要再深挖一遍才放心。早春的气温还很低,河道里的风仍像刀子一样硬。但父亲像挖战壕一样,不一会儿就热得脱掉了身上的棉袄。父亲每次从地下掏出一块小石头,就像拣到了金元宝一样高兴。扔掉石头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一个石头四两油哩。
河滩地里长庄稼,长得更多的是杂草。尽管父亲的板锄抡得呼呼生响,杂草还是悄悄地从地缝里钻出来,见风就长;锄禾日当午的三伏天,父亲的孽果就大了。河滩地里更喜欢涨大水。涨一场大水后,河滩地里一片狼藉,庄稼叶子上糊弄着脏乎乎的淤泥,父亲又得重修一遍河滩地了。就这样天道轮回着,父亲洒在那片河滩地上的汗水,慢慢地滋润到了汝河水里流淌着。
父亲是农民,一辈子就认得土地,认得粮食。不论啥样的地块,到了父亲手里都能焕发出生机。瘠薄不耐旱的土地,父亲从坡上弄回木拉叶肥田;低洼不平整的土地,父亲削高垫低地整治成水浇地;年久失修的水毁荒地,父亲垒石砌堰后,整修一新的农田比原来的面积大了许多;沟垭里别人嫌远的抛荒地,父亲种上了洋芋;黄土梁顶上多半亩的高山田,父亲撒上了高粱种;对窝崖上脸盆大的几个石窝子,父亲垫上了土,栽上了南瓜秧。中秋时节,瓜藤黑黝黝地绿得发亮,一个个滚瓜肚圆的老南瓜,笑眯眯地在石堰上晒太阳,金灿灿地像一枚一枚的劳模奖章。
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背有点驼了。但父亲依然一个人在堡子洼里修梯田。父亲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在山上煮面条吃,缺盐少调和地凑合着。堡子洼的烤树叶黄了又青了,崖畔上的柿树叶红得发紫时,四个台阶近乎两亩的水平梯田修成了。父亲赶在霜降前种上了麦子。来年端午节割麦时,堡子洼的麦子厚实得一层一层地割不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那年碾场的劳动情景如在眼前。
五黄六月的天际上光溜溜地,连一绺云彩都没有,白花花的太阳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这正是碾场的好光景。父亲戴着老草帽,右手挥着柳条鞭子,左手挽着青麻缰绳,“吁、吁”地使唤着牲口碾场。戴着牛笼嘴的黄牛拉着沉重的碌碡一圈一圈地转着同心圆,麦秆嗤嗤啦啦地抖动着,直到麦秆碾得服服帖帖不发一声了,就到了清场的时候了。父亲用木叉撩起麦秆,白花花的新麦香气在小南风里就飘出老远。到了晚上,母亲在月光下簸麦子,孩子家在麦草堆上翻跟斗,父亲坐在麦堆旁有滋有味地听着秦腔戏,看得出父亲心底的高兴来。
父亲小时候挨过饿,经历过种田的千辛万苦,爱惜粮食是出了名的。父亲一年年收回来的粮食吃不完,就做了几条大柜存起来。到后来,柜子里装不下了,只好忍痛卖掉粮食。每当购销站的农用车开到我家院子里时,父亲总是舍不得多卖。粮食拉走了,父亲觉得心里空荡荡地不踏实。到晚年,实在翻晒不动陈年旧粮了,只好整车卖掉了一些粮食。父亲去世后,二哥开着机动三轮往返了粮站好几趟,才把剩余的粮食卖掉。这次卖粮的钱,安葬父亲都用不完。想起小沈阳“人走了,钱还在”的伤心话,我的眼泪哗哩哗啦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