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我重新认识中国的起点
文章字数:5406
本报记者 汪 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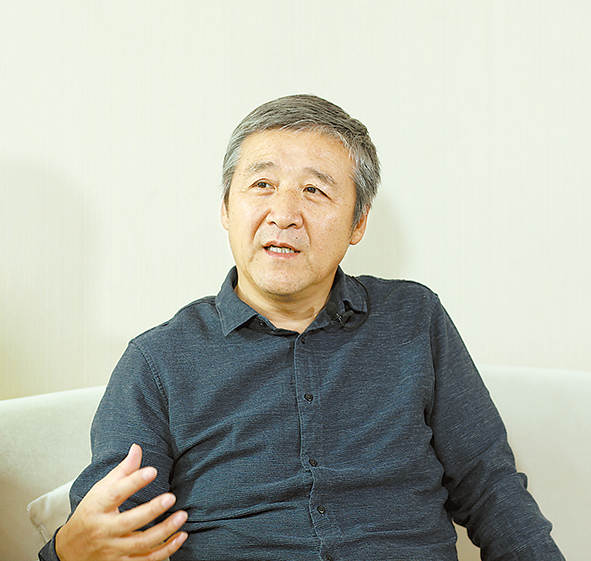
9月24日,在由商洛日报社和丹凤县委、县政府主办的“大美秦岭媒体论坛暨社长(总编)看商洛”主题活动上,中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做了主题演讲。会前,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汪教授,您好!感谢您前来参加这次活动并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方面卓有才华的研究者,不但研究成果丰硕,而且知识结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非常独特,众多学者和读者都期待您传经送宝。能否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
汪晖:我是江苏扬州人,年轻时候在扬州师范学院求学,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大学,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到北京跟随唐弢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直到2002年。这期间我也有很多经历在国外,1992年至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之后回到国内继续在研究所工作,中间穿插地去过哥罗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以及日本的高校做访问、研究。1996年至2007年,应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女士的邀请,我去兼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那时候就一边做研究,一边编辑杂志。2002年,我从社科院调到了清华大学,一直到现在就在清华大学教书。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当中,有两段经历是特别的,也是与后来年轻人相比不同的地方,一次就是,我中学毕业后高考还没有恢复,就到工厂做临时工,后来经正式分配做徒工,先后在罐头厂、纺织厂、无线电厂干过,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个经历;再一段就是跟商洛有关系,1990年,我到山阳县工作了大半年时间,第一次深入山区,也是第一次到农村基层工作,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
记者:您刚才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被安排到商洛工作的那段经历让您记忆深刻。您当时在山阳主要是做什么工作?今天再次来到商洛,您有什么感触?
汪晖:当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认为年轻人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尤其是对乡村基层的认识和理解很欠缺,就把一些年轻人送到基层进行锻炼,我就被安排到山阳县委宣传部。那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生长在江淮平原,之前从没有到过大山里面,尤其是秦岭的山区,所以刚来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不习惯,有距离感。所谓的距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空间,那个时候交通还不发达,火车也不像现在这么快,我记得从北京到西安坐了17个小时,再从西安坐公共汽车到山阳县,根据天气状况,如果下雨车子就走得更慢,大概八九个小时才能到。另一个就是现实生活的差别很大,从城市到乡村的落差感,无论是与北京还是我的家乡相比,区域差别、城乡差别都是很大的,商洛地区当时是比较贫困的,那种贫困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然而,对我来讲,看似艰苦的基层锻炼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北京,我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状况,都是一种间接了解,脑子里面缺少对商洛这样的农村地区的直观概念和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商洛当时的经济社会面貌,我认为是有代表性的,在广大的内地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地区的发展现状、遇到的困难,以及干部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与我们在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了解到的,是有深刻距离的,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是有缺陷或偏颇的。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学者,能真正看到问题的本身,这是我在山阳工作那一段时间最大的收获。
我在山阳一开始是在宣传部工作,刚开始不知道到乡村里面做什么,但是真正下去以后,我就发现一些听起来很抽象的概念,到了基层都是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民成为自由自在的个体户,打牌赌博、封建迷信等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盛行;土地承包到户了,但是家族家庭之间,围绕地界纠纷,发生的冲突是很多的;由于贫困面广,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照明用的依然是油灯,生活十分艰苦;医疗报销非常困难,就连机关干部公费医疗报销都经常是断档的,等等。我当时就跟着县里面的一些干部和同事下村入户,去了解这些情况,研究到底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干部群众都非常努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县里只有两辆吉普车,干部都是骑着自行车下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做事情,很多人周末也不休息,我也借辆自行车,跟他们下到村里面。在山区骑自行车是不容易的,印象中有一次下暴雨,路被冲毁了,我们走了几个小时才到一个学校,一看学校的水电还没有恢复,就去各家动员,然后和群众一起修复河岸、重建学校,那种真切感受让我重新开始认识中国的农村。
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来商洛,一路上走得都是高速公路,沿途楼房林立,满眼绿荫,仅是目睹也知道变化太大了,跟当年来商洛的感受,以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种变化让我大为吃惊,也深感欣慰。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再一次引发我的思考和探究的欲望,改革开放带来城乡巨变,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特点,过去现在未来,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变贫困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因素等等,都是我将要分析研究的内容。
记者:您担任《读书》执行主编十多年,《读书》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年销量十几万册。《读书》发表的文章,涉及对“三农”问题、农村医疗保障等问题的探讨,从而引起社会与媒体的重视,促使政府做出回应,改变政策。您当时的办刊理念是什么?
汪晖:《读书》是1979年创刊的,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个开放的象征,编发的主要是文史类型的内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全球化,都有较大的发展,这个发展是根本性的,改变了原有的组织管理体系,那很显然,如果继续完全用过去的理念陈旧的方式来理解变化、变迁,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一个思想空间,引导不同深度思考,老中青学者、中外不同地区的学者,在这个空间当中把他们的思考和认识带进来,从而推动思想大讨论、文化大讨论,这是我们当时编辑工作的一个基本思路。
1996年我担任《读书》主编以后,在保持文史知识部分内容的同时,很快开辟一些专栏,其中有关于乡村的栏目,就是专门召集一些学者,来讨论中国乡村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让不同的声音、观点、理念在一起碰撞,让人们逐渐更加清晰地准确地看见真实的问题,从而引发更广泛地关注,给决策者提供思路。有一次在一个编辑手记里,我专门写过我在山阳的经历,就是通过山阳怎么去看待理解我国中西部乡村的问题,通过比较来观察当时的有关制度变革。就我个人来说,把诸多民生问题带入到社会问题讨论中,是跟我在山阳的工作经验有一定关系的。
那个时候不仅“三农”问题,还有医疗体制、教育改革等一系列话题,不但一般的学术界甚至政府,也不是特别清楚里面的危机有多大,所以那时候很多学者的文章在《读书》发表,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读书》只是一个文化思想领域的刊物,但是由于它的关注角度和社会影响,与实际情况,以及发展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发生关联,在为读者提供了多元的、对称的信息,形成反思的讨论空间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后来政策层面的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是令人很高兴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记者:您最初的学术方向是文学评论,重点是鲁迅思想研究,您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对鲁迅很多问题的讨论,至今仍被认为是典范作品。后来您主要侧重于思想史领域,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汪晖:我从1988年到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从事鲁迅研究,《反抗绝望》前半部分很多成分已经是思想的研究,不是完全的文学研究。之后我开始做“五四”精神研究,又从“五四”转向晚清文化思想的研究,内容一直推向越来越早的历史了,所以就逐渐地,把研究的重点变成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但关于鲁迅的作品以及鲁迅研究的文章,我一直在读,现在也会读,因为鲁迅思想不仅是我研究的对象,也是我思考问题的重要方式,也可以说已经渗透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
我到商洛来的时候,也带了一箱子书来,这些书很多是设计思想实验的,过去毕竟是书生啊,到了山阳,除了宣传部安排的事情之外,我自己也做一些调查。我当时特别有兴趣的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运行过程,尤其是改革之后基层政权工作的开展、绩效的衡量,甚至体制的运行,这些问题过去并不在我的研究领域,关于基层政权工作,是我到了山阳之后才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时人民公社解体之前,基层的管理体系是通过公社、大队、小队对乡村的管理,实际上是通过集体化的土地关系来完成,但是改革之后,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乡村管理,又遇到了什么样的矛盾和困惑,引起了我的好奇。举个简单的例子,土地改革时,连公房也分掉了,乡村党组织党支部也没地方开会,变得涣散自由,而过去党支部是乡村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挥所”,那之后怎么办、怎么管?而且区乡一级政府没有直接对土地的支配权,财政又极其贫弱,如何去管理乡村,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山阳面临这些问题,我亲眼看见,因为地界纠纷两个家族发生械斗,乡政府区政府都做了处理决定,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类似这样的情况经常碰到,即使发现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其实这在当时的乡村地区非常普遍。
坦白地说,我在来商洛之前,在进入乡村做社会调查之前,我脑子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完全不懂,不理解这些现象也就不懂基层政权管理遇到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幸运的是,当年跟我一起来的年轻同学,有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法律研究所的、人口研究所的,还有国际研究所的,各自的专业背景不同,我们一起来收集材料,一起做分析研究,完成了多个课题研究。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大学专业门类多也很专业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学生都是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多少社会经验,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如果不去接触社会,没有提出问题和经验,还是思考不够真正深入,所以这也是我研究社会思想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从李白的《蜀道难》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从王维的《辋川图》到山水田园诗派,面对秦岭,历代文人或挥笔豪放,书写秦岭的雄浑、奔放,或淡雅、内敛,挥洒自己对秦岭山水的感悟。请谈谈您对秦岭文化的理解?
汪晖:秦岭在地理上是我国南北方的分界山,在文化上却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处、南北文化的融合地。它是中国文明形成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地区,古人的诗歌,讲秦岭的非常非常多,过去我们读韩愈的诗,王维的诗。后来从秦岭走出了很多著名的作家,仅商洛就走出了比如贾平凹、陈彦这样的文学大师,从他们的作品依然能读出浓浓的秦岭文化的气息。这次来商洛前,我去了河南郑州、登封、洛阳,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到商洛,看一看最早的考古学上的这些文化,从西安半坡到郑州的二里头,历史是那么久远,历史文明却在延续,中原的整个历史文化大气磅礴,就是在秦岭这样一个特殊地域里面发展起来的。从唐宋到明清,秦岭和与它相关联的这些区域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纵观同属秦岭文化区域的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历史上多少故事发生在这些地方,所以说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确实要理解秦岭文化。到了近现代,我们也都知道,社会变迁的很多故事都跟它有关,所以说秦岭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区,它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的发生地,同时也是一条文化纽带。
记者:听说您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商洛:我重新认识中国的起点》,为什么确定了这样一个主题?
汪晖:对我来说,商洛是我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很多次的变化,我是从江淮流域出来的人,之后到北京,在来商洛之前,待在学院里,生活在城市里,所以对中部、内地、山区地区,我是没有太多概念和了解的。商洛给了我不同的体验不一样的经历。而且,在商洛工作的时期,是中国和世界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对我来讲,一个思考重新开始,因为无论做文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还是社会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中国最基层的理解、观察。所以在这儿的这个经验,实际上是渗透在我以后工作里面的。所以我把它看成是我人生道路和思考历程中的一个很重要新的起点。当然人生有很多起点,但这个起点是最独特的起点。
人物介绍
汪晖,195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学人》丛刊创办主编之一,《读书》杂志执行主编。2002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与学习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2018年1月,获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社会理论和民族区域研究方面均有重要成就。迄今已发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等中文学术论著近20种,论文上百篇,英文论文约50篇。目前已出版包括英文、日文、韩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斯诺文尼亚文等作品25种。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和英国《远景》(Prospect)期刊评选的全球“百名知识分子”(Top100intellectuals)。2009年,入选德国《时代》周报“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2010年,成为美国亚洲学会年会(AAS)首位来自中国的基调演讲人。曾应邀在澳洲亚洲学会年会、英国中国学会年会等重要学术活动中发表基调演讲,并任若干重要国际学术刊物和机构的编委、理事。2013年,入选英国《远景》评选“世界思想家”(WorldThinkers)的65人名单,与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同获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2018年,获德国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