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历险
文章字数:1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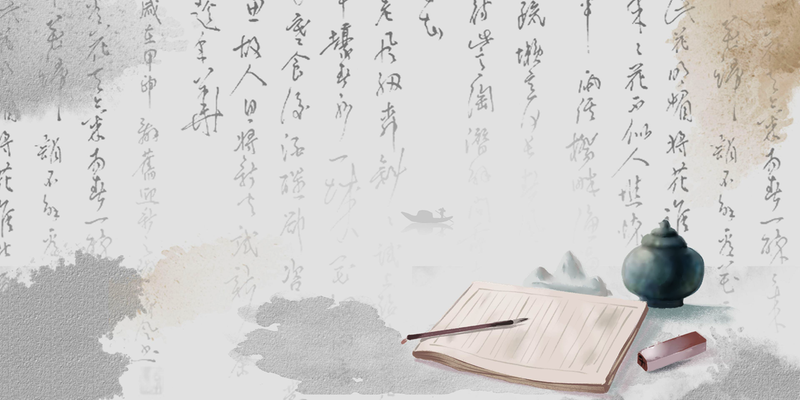
从偶发兴致随性涂鸦,到视写诗为一种生命形态、一种生活方式,在持续的诗歌实验和探索中,好像时光一点点把我向一个诗人引导、锤锻、淬炼、磨砺,我也越来越心安理得接受了“诗人”这一称谓,并一步步筑建着自己的诗歌理念和诗歌样态。当然,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每一个诗人都会这样,如同瓜熟蒂落,如同水到渠成,没有什么玄机,也没有什么可说道的必要。值得一提的,是自己每每对这个熟悉世界里隐藏的陌生和神秘,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感悟之后,所产生的激动与欢欣。这激动与欢欣,如爱情,又如引擎,牵引着我走在满布沟壑、荆棘和孤独的诗歌路上,一走就是数十年。
但我还是对诗歌生出了些许不满。它局限了我。总感到,发现、认识了那么多,积累、思考了那么多,而进入诗歌的,往往只一个片段、一小丁点,大量素材和资源如闲物般被抛弃,一条江只掬起一捧水,一棵树只制作了一双筷子,多无奈,多遗憾。哈,这也许是我的偏见,错怪了诗歌。写不出史诗级的鸿篇巨制,完全是个人功力不够的问题,而诗歌,默默承受着我的不满,背负着我施与的罪名,却没有一点离我而去的意思。我和诗歌共同迁就、成全我写作的办法,便是把那些自己无愿无力入诗的东西,从大脑的某个记忆的储藏室拽拉出来,加工组装成另外的部件,使其获得重新利用。这就有了我的散文写作,仿佛它在弥补着诗歌的过错。因而我的散文,大多是我诗歌思维的延展,贯通着我诗歌的气息。这么说来,其实我应该是诗歌的受益者,我所认为的那些束缚和局限,正好为我一用,变作我涉足不同文体、开拓文学宽度和深度的手段。如果有读者愿将我的一些散文当诗来读,我会乐见这样的阅读。
原来,经历的生活和遇见的物象,它们的用途和意义是多方面的,都会这样或那样地与我交集,作用于我,就像春的温暖、夏的炎热、秋的舒适、冬的寒冷,不同气象,让你尽知生活滋味,少了哪一个季节和物候,自然之态、人之生存场域和文学之原生镜像,都显残缺;就像一条江,绝非吝啬到予我一捧水,无论何时,它都会慷慨地给我一个心灵的、文学的阔大世界;就像一棵树,可以附着万千意象,可以安顿众多生命,绝非只想做一只鸟的栖息地、一阵风的感应物。而那些经历过的时代大事件,就更不用说了。它们之于我的写作,如同源泉。一旦安静下来,过往生活的某个大场景或者小细节,就会走向我,萦绕成我的思绪,触摸着我的笔端,一次次推动我的创作,纠正着我的偏执和懒惰。
把自己写作中的这些“隐私”说出来,很是忐忑。揭了诗歌像一个人一样挑剔得近乎苛刻的短板,是不是冒犯了诗歌的高贵?说散文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是不是伤害了散文的尊严?两种文体让我都得罪了,不知它们能否宽恕我?我正在写以及还未去写的文字们,还会不会继续垂青我、赐福我?这种想法多么多余、多么可笑呀,文学那神一样的气度和气场足以包容整个宇宙,它播撒的友善和爱足以惠及任何人群。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人情物理跃然纸上,天地精神力透纸背。虽然我还在期待着下一部作品能帮我实现这个心愿,但我始终提醒自己,必须恪守并传递对万物万事的真实情感,对生活生命的本真揭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配的言说系统,必须对得起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汉语。
而从古今中外已有经典里吸取营养、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不断突破甚至彻底颠覆自己,努力超越经典,才能抵达另一种界面,才称得上对伟大的汉语文学有所贡献。写作者们深知的事理,我又啰唆一遍,实在是因我的感悟力、想象力、语言掌控力有限,找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词汇来说服自己开辟新的路径去攀越文学的峰顶。
所以,我得自加压力、自设难度。这犹如历险,可能陨落悬崖,继续平庸;可能渡至彼岸,成就不凡。而用文字挑战文字、在文字里历险,恰是作家的秉性,谁甘守平庸,谁不想出手一试?反正我想,成不成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