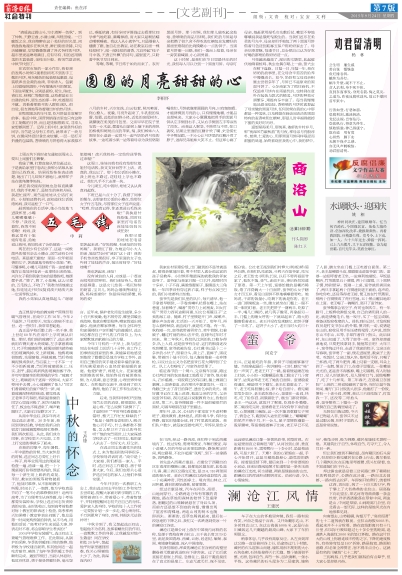蛮爷
文章字数:2047
我家在村里辈份低,出门碰到的不是爷就是叔,都得恭敬地叫着,要不村里人就会说这家的孩子没教养。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数我的邻家蛮爷了。蛮爷家与我家只隔一口水井,他那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满脸络腮胡子,眼睛是大三角眼,一年四季没有穿过新衣裳,样子有点凶巴巴的,我们小娃都有点怕他。
蛮爷先是我们队里的队长,每天清早,他一手拿着旱烟袋,一手卷成喇叭状搭在嘴上,站在巷道,扯着嗓子,喊着“男劳力上河割麦,妇女打场”“男劳力西河边砌河堤,妇女公场簸豆子”之类的派工活。随即,村子里便是开门声、咳嗽声、脚步声杂沓着,忙活的一天开始了。那年月,再怎么春种秋收,流血流汗,就是吃不饱。有一年,秋收刚一完,蛮爷就带着男劳力,牵牛背锅,扛着被子,翻过村前的南山去开荒,直到快过年时才回来。第二年秋天,我们队比别的队口粮多得多,队上人说,还是蛮爷有办法,这打的粮食还没吃到嘴里,蛮爷就被告发,公社冀书记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留着分头,黄上衣,蓝裤子,黑皮鞋,带着四个基干民兵,每人胸前抱着一支冲锋枪,以反社会主义为名把蛮爷五花大绑押到了公社。队上人有啥吃了,可蛮爷却受罪了。
临近春节的一个周六,父亲骑车回家,路过公社两岔河的农田基建工地看见了蛮爷,他光着头,衣衫褴褛,一双胶鞋已没有后跟,腿上缠着白裹缠,上面渗着血,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双三角眼已失去了昔日的锋芒,透出乞求的柔光。刚好冀书记在工地上巡查,他是父亲的学生,父亲说蛮爷有病,农民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放他回去吧,第二天,蛮爷便披着一件不是很破很烂的黑袄,叼着旱烟袋在巷子里溜达。
那年月,县、区、公社的干部常常下乡进村整班子,路线教育,批林批孔,抓阶级斗争,有时也修路,搞农田基建会战,到了村里就吃派饭。我们队户数少,就每家连着吃两天,年终队里给分粮分钱。公社老王派到我们村修大(荆)板(桥)简易公路,在我们队吃派饭,头两天在蛮爷家,吃完之后,老王给支书和队长说,以后不要再派蛮爷家了,他吃不饱,受气,还说不出,事后我们知道了原委。第一天上午饭,蛮婆给做的是糊汤稀饭,烙了洋瓷碗大一个白面饼,蛮爷的幺女子瞎女才四五岁,看见白面饼不停地嚷嚷着要吃。她妈说,干部的饭量小,吃剩下的就是你的。老王一进门朝案板边一坐,瞎女就坐在门槛上一眼不放一眼的盯着。老王先把饼子一掰两半,吃掉了一半,喝几口糊汤,就几筷子酸菜,再拿起另一半,门槛上的瞎女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瞪大的眼睛看着老王。老王并没有发现瞎女,把饼子掰了一半吃了。这饼子太小了,老王当时大约三十出头,正是能吃的年龄,那饼子可能刚够塞牙缝。当他拿起最后一块饼刚咬一口时,瞎女“哇”的一声哭了,把老王吓了一跳,接着便是睡在地上打滚,小小的一双脚硬是在地上蹬出了几个窝窝子,边哭边骂老王吃了她的白面饼。蛮婆脸羞得通红,硬是哄不下瞎女,老王红着脸走了。下午,老王吃得胆膻心惊,萝卜烩白面片。看见碗里菜多面少,老王就吃得小心,蛮婆在一边说,快吃,吃了给你舀,别饿着肚子,谁出门都没背锅。老王一听这话,就放开了喉咙,吃得扑扑噜噜。第二碗没吃完时,蛮婆看老王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心想刚做三碗饭,这一次不能再惹瞎女子哭了,情急之下,跑到炕头边坐在尿罐上,“唰唰唰”的尿声不绝于耳,不一会儿,屋子里便弥漫着一股尿臊味,等蛮婆提着裤子出来,老王早已不见了人影,瞎女坐在门槛上正吃着白面条。第二天,老王是硬着头皮,僵着脸走进蛮爷家门的。蛮婆一边招呼着老王坐,一边麻利地端饭。早饭是糊汤,竹笊篱里五个蒸馍,两个白面馍,三个黑麸子馍,特别怪异。饭刚一上桌,蛮爷就担粪回来了,两只手拿起两个白馍递到老王面前,连声说,你吃你吃,还没等得老王接,便又放在竹笊篱里,那两个白馍便成了虎行雪地,五个黑点醒目地印在上面。老王喝了一碗糊汤,离开了蛮爷家。
蛮爷做事会钻空子,有时也吹吹牛。有一年腊月,上板桥收购组交猪,自己的猪和别人的一比,就是猪瘦毛长,他一咬牙,买了一包宝成烟,准备送给验收猪的人。排队到自己时,才发现验收员是村支书东山的外甥,便灵机一动,说猪是东山的,验收员用手压压猪脊梁骨,大声说,管你东山不东山,五等,手却拃着四个指头。此后回村,东山知道了,大骂了蛮爷一回。蛮爷却喜滋滋地说,只要把钱拿到手,随他骂去吧!大年三十,蛮爷绕过井台,走进了我家的院子,父亲正在写春联,蛮爷要了一副,便走进屋里,数桌子上的菜。吃饭时,父亲让他入坐,他死活不肯,只喝了三杯酒,吃了两片肥肉,嘴上叼着一支烟,耳朵上别了一支烟,便出了门,在巷子里溜达,一张嘴油光光的,还是舍不得擦掉,嘴上叼着烟,有人时抽两口,没人时就掐灭,见人便哈口气,说他喝醉了,吃了十几样菜。第二年春天,在洛南卫东国防厂上班的二哥说他碰到了蛮爷,当时正是午饭时间,餐厅门口讨饭的人很多,他刚打了一份饭,便有一个老头说,师傅,我已三天没吃饭了,打发我一下,还没等二哥抬头看,蛮爷便将二个馒头一份菜倒在自己的碗里端走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今天早已物是人非,蛮爷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但村子里的人还是常常说他。
蛮爷先是我们队里的队长,每天清早,他一手拿着旱烟袋,一手卷成喇叭状搭在嘴上,站在巷道,扯着嗓子,喊着“男劳力上河割麦,妇女打场”“男劳力西河边砌河堤,妇女公场簸豆子”之类的派工活。随即,村子里便是开门声、咳嗽声、脚步声杂沓着,忙活的一天开始了。那年月,再怎么春种秋收,流血流汗,就是吃不饱。有一年,秋收刚一完,蛮爷就带着男劳力,牵牛背锅,扛着被子,翻过村前的南山去开荒,直到快过年时才回来。第二年秋天,我们队比别的队口粮多得多,队上人说,还是蛮爷有办法,这打的粮食还没吃到嘴里,蛮爷就被告发,公社冀书记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留着分头,黄上衣,蓝裤子,黑皮鞋,带着四个基干民兵,每人胸前抱着一支冲锋枪,以反社会主义为名把蛮爷五花大绑押到了公社。队上人有啥吃了,可蛮爷却受罪了。
临近春节的一个周六,父亲骑车回家,路过公社两岔河的农田基建工地看见了蛮爷,他光着头,衣衫褴褛,一双胶鞋已没有后跟,腿上缠着白裹缠,上面渗着血,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双三角眼已失去了昔日的锋芒,透出乞求的柔光。刚好冀书记在工地上巡查,他是父亲的学生,父亲说蛮爷有病,农民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放他回去吧,第二天,蛮爷便披着一件不是很破很烂的黑袄,叼着旱烟袋在巷子里溜达。
那年月,县、区、公社的干部常常下乡进村整班子,路线教育,批林批孔,抓阶级斗争,有时也修路,搞农田基建会战,到了村里就吃派饭。我们队户数少,就每家连着吃两天,年终队里给分粮分钱。公社老王派到我们村修大(荆)板(桥)简易公路,在我们队吃派饭,头两天在蛮爷家,吃完之后,老王给支书和队长说,以后不要再派蛮爷家了,他吃不饱,受气,还说不出,事后我们知道了原委。第一天上午饭,蛮婆给做的是糊汤稀饭,烙了洋瓷碗大一个白面饼,蛮爷的幺女子瞎女才四五岁,看见白面饼不停地嚷嚷着要吃。她妈说,干部的饭量小,吃剩下的就是你的。老王一进门朝案板边一坐,瞎女就坐在门槛上一眼不放一眼的盯着。老王先把饼子一掰两半,吃掉了一半,喝几口糊汤,就几筷子酸菜,再拿起另一半,门槛上的瞎女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瞪大的眼睛看着老王。老王并没有发现瞎女,把饼子掰了一半吃了。这饼子太小了,老王当时大约三十出头,正是能吃的年龄,那饼子可能刚够塞牙缝。当他拿起最后一块饼刚咬一口时,瞎女“哇”的一声哭了,把老王吓了一跳,接着便是睡在地上打滚,小小的一双脚硬是在地上蹬出了几个窝窝子,边哭边骂老王吃了她的白面饼。蛮婆脸羞得通红,硬是哄不下瞎女,老王红着脸走了。下午,老王吃得胆膻心惊,萝卜烩白面片。看见碗里菜多面少,老王就吃得小心,蛮婆在一边说,快吃,吃了给你舀,别饿着肚子,谁出门都没背锅。老王一听这话,就放开了喉咙,吃得扑扑噜噜。第二碗没吃完时,蛮婆看老王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心想刚做三碗饭,这一次不能再惹瞎女子哭了,情急之下,跑到炕头边坐在尿罐上,“唰唰唰”的尿声不绝于耳,不一会儿,屋子里便弥漫着一股尿臊味,等蛮婆提着裤子出来,老王早已不见了人影,瞎女坐在门槛上正吃着白面条。第二天,老王是硬着头皮,僵着脸走进蛮爷家门的。蛮婆一边招呼着老王坐,一边麻利地端饭。早饭是糊汤,竹笊篱里五个蒸馍,两个白面馍,三个黑麸子馍,特别怪异。饭刚一上桌,蛮爷就担粪回来了,两只手拿起两个白馍递到老王面前,连声说,你吃你吃,还没等得老王接,便又放在竹笊篱里,那两个白馍便成了虎行雪地,五个黑点醒目地印在上面。老王喝了一碗糊汤,离开了蛮爷家。
蛮爷做事会钻空子,有时也吹吹牛。有一年腊月,上板桥收购组交猪,自己的猪和别人的一比,就是猪瘦毛长,他一咬牙,买了一包宝成烟,准备送给验收猪的人。排队到自己时,才发现验收员是村支书东山的外甥,便灵机一动,说猪是东山的,验收员用手压压猪脊梁骨,大声说,管你东山不东山,五等,手却拃着四个指头。此后回村,东山知道了,大骂了蛮爷一回。蛮爷却喜滋滋地说,只要把钱拿到手,随他骂去吧!大年三十,蛮爷绕过井台,走进了我家的院子,父亲正在写春联,蛮爷要了一副,便走进屋里,数桌子上的菜。吃饭时,父亲让他入坐,他死活不肯,只喝了三杯酒,吃了两片肥肉,嘴上叼着一支烟,耳朵上别了一支烟,便出了门,在巷子里溜达,一张嘴油光光的,还是舍不得擦掉,嘴上叼着烟,有人时抽两口,没人时就掐灭,见人便哈口气,说他喝醉了,吃了十几样菜。第二年春天,在洛南卫东国防厂上班的二哥说他碰到了蛮爷,当时正是午饭时间,餐厅门口讨饭的人很多,他刚打了一份饭,便有一个老头说,师傅,我已三天没吃饭了,打发我一下,还没等二哥抬头看,蛮爷便将二个馒头一份菜倒在自己的碗里端走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今天早已物是人非,蛮爷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但村子里的人还是常常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