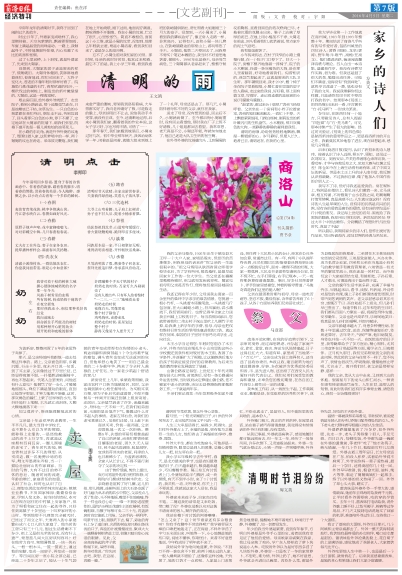卖屋
文章字数:1476
为盖新房,整整闲置了5年的老屋终于卖掉了。
那天,是父亲特地叫我跟他一道去处理这件事的。路上,父亲面色阴郁,步履沉缓,行走十多里,竟未开口说一句话。到了买主家,父亲像经过千万里长征,已经显得疲惫不堪,一扑塌跌进破圈椅中,再也不想起来。代笔人念罢契约,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他惘然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摇摇头,耷拉下满是皱纹的眼皮,直到让他签字那刻,才努力地掀开条缝,这时,那灰褐色的瞳仁上蒙了层厚厚的水光,等抖抖地拧上笔帽,水光就汇成泪珠,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
知父莫若子,惟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父亲是个年近花甲的老教师,一生平平凡凡,最大当到中学校长,也不算什么引以为荣的辉煌,能称得上业绩的,一是经他教过的成千上万学生,再就是这座拥有四间瓦房、一圈儿围墙的老宅了。青年时代的他,倒也曾有过许多不凡的理想:从戎戍边,做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舞文弄墨调朱弄粉,当一个描绘壮丽河山的作家画家。当时的气势,大有不达目的势不休的悲壮。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家庭责任的加重,认识了社会,同时也认识了自己,理想也因此变得单纯实际起来:兢兢业业教书,不负国家俸禄;勤勤俭俭治家,尽到人伦义务。按当时的情况,本可以在现在居住的中村镇上安家落户,但为了照看和叔父住在一起的爷爷,只好住到离镇子十多里远一个叫罗家坪的小山村。等到他那不凡理想完全破灭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夫妻两人的小家庭繁衍成六七口人的大家庭了。他当时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刨过生活费剩不下多少,祖上又是很光荣的贫农,没有什么遗产,要想盖几间大瓦房谈何容易?好在他劳力尚可,寒假暑假里,一块一块石头,一根一根木头,一筐一筐泥土,通过他的肩膀,变成一间房子,再变成一间房子。等四间瓦房一座小院全部立起,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了,他从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变成背脊有点佝偻的小老头,两边肩膀和颈窝耸起3个今生再难平复的瘤包,满头青丝也变成无法返回的灰白,但他却舒心地笑了——用自己最金贵的二十多载年华,换来了令全村人羡慕的上好住宅,为一家老少筑起个舒适的窝儿!
新房没住上几年,承蒙政策照顾,我家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居民,其时,父亲也调到镇中心校任督导员。为买粮买菜方便,更为子孙后代前途着想,不得不像候鸟一样离开旧巢迁到镇上租房寄居。迁居后,父亲猛然衰老了许多,话越来越少,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在我们姐弟面前,无端的显出低声下气,像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老家左邻右舍,对我们的老宅垂慕已久,见我们迁居,马上赶下来商谈买卖,价钱一涨再涨,父亲却固执地一次又一次拒绝。整整5年,失望的邻居们相继盖起了自己的新屋,而我们那曾经眩目耀眼的老屋,因久久无人居住,经不起风雨剥蚀、蚁鼠洞穿,变成名符其实的老屋,问津的人也日渐稀少了。为盖新房凑钱,全家人从长计议,不得不强行剥夺了父亲的决定权……
由于售价低廉,契约上提出,卖方可将屋外的部分附件拆除,可将院内几棵成材的树木砍走。父亲绕着老屋转了好几圈,这儿拍拍,那儿摸摸,连厕所面上的大石条也踩了好几遍(为从未消的洪水中捞它,父亲差点儿丢了性命),头不停地摇,嘴里不住地喃喃,终于一件也没忍心动……唯一不损伤老屋整体的,是院内5棵正茂盛生长的红椿树,有饭碗粗细,当檩子每根可卖二三十无,再盖新房时肯定能派上用场。父亲手执一柄利斧,咬紧牙闭上眼,狠狠砍下去,偏了,旁边的青石上多了道白痕,光滑的树皮却只豁出条浅浅的口子,浑浊的汁液慢慢浸出,聚成大大一滴顺着树根渗进土里,很像只暗自伤心流泪的眼睛。见此,父亲高高扬起的斧子软软塌下来,呆愣半晌,转身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屋、再睡一晚。”
那天,是父亲特地叫我跟他一道去处理这件事的。路上,父亲面色阴郁,步履沉缓,行走十多里,竟未开口说一句话。到了买主家,父亲像经过千万里长征,已经显得疲惫不堪,一扑塌跌进破圈椅中,再也不想起来。代笔人念罢契约,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他惘然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摇摇头,耷拉下满是皱纹的眼皮,直到让他签字那刻,才努力地掀开条缝,这时,那灰褐色的瞳仁上蒙了层厚厚的水光,等抖抖地拧上笔帽,水光就汇成泪珠,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
知父莫若子,惟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父亲是个年近花甲的老教师,一生平平凡凡,最大当到中学校长,也不算什么引以为荣的辉煌,能称得上业绩的,一是经他教过的成千上万学生,再就是这座拥有四间瓦房、一圈儿围墙的老宅了。青年时代的他,倒也曾有过许多不凡的理想:从戎戍边,做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舞文弄墨调朱弄粉,当一个描绘壮丽河山的作家画家。当时的气势,大有不达目的势不休的悲壮。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家庭责任的加重,认识了社会,同时也认识了自己,理想也因此变得单纯实际起来:兢兢业业教书,不负国家俸禄;勤勤俭俭治家,尽到人伦义务。按当时的情况,本可以在现在居住的中村镇上安家落户,但为了照看和叔父住在一起的爷爷,只好住到离镇子十多里远一个叫罗家坪的小山村。等到他那不凡理想完全破灭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夫妻两人的小家庭繁衍成六七口人的大家庭了。他当时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刨过生活费剩不下多少,祖上又是很光荣的贫农,没有什么遗产,要想盖几间大瓦房谈何容易?好在他劳力尚可,寒假暑假里,一块一块石头,一根一根木头,一筐一筐泥土,通过他的肩膀,变成一间房子,再变成一间房子。等四间瓦房一座小院全部立起,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了,他从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变成背脊有点佝偻的小老头,两边肩膀和颈窝耸起3个今生再难平复的瘤包,满头青丝也变成无法返回的灰白,但他却舒心地笑了——用自己最金贵的二十多载年华,换来了令全村人羡慕的上好住宅,为一家老少筑起个舒适的窝儿!
新房没住上几年,承蒙政策照顾,我家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居民,其时,父亲也调到镇中心校任督导员。为买粮买菜方便,更为子孙后代前途着想,不得不像候鸟一样离开旧巢迁到镇上租房寄居。迁居后,父亲猛然衰老了许多,话越来越少,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在我们姐弟面前,无端的显出低声下气,像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老家左邻右舍,对我们的老宅垂慕已久,见我们迁居,马上赶下来商谈买卖,价钱一涨再涨,父亲却固执地一次又一次拒绝。整整5年,失望的邻居们相继盖起了自己的新屋,而我们那曾经眩目耀眼的老屋,因久久无人居住,经不起风雨剥蚀、蚁鼠洞穿,变成名符其实的老屋,问津的人也日渐稀少了。为盖新房凑钱,全家人从长计议,不得不强行剥夺了父亲的决定权……
由于售价低廉,契约上提出,卖方可将屋外的部分附件拆除,可将院内几棵成材的树木砍走。父亲绕着老屋转了好几圈,这儿拍拍,那儿摸摸,连厕所面上的大石条也踩了好几遍(为从未消的洪水中捞它,父亲差点儿丢了性命),头不停地摇,嘴里不住地喃喃,终于一件也没忍心动……唯一不损伤老屋整体的,是院内5棵正茂盛生长的红椿树,有饭碗粗细,当檩子每根可卖二三十无,再盖新房时肯定能派上用场。父亲手执一柄利斧,咬紧牙闭上眼,狠狠砍下去,偏了,旁边的青石上多了道白痕,光滑的树皮却只豁出条浅浅的口子,浑浊的汁液慢慢浸出,聚成大大一滴顺着树根渗进土里,很像只暗自伤心流泪的眼睛。见此,父亲高高扬起的斧子软软塌下来,呆愣半晌,转身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屋、再睡一晚。”